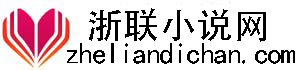9、第9章(2/5)
回头看向曲龄幽,眼里有希冀,显然是希望曲龄幽能说服明墨。曲龄幽微怔。
明墨注意到后也看向曲龄幽:“龄幽。”
这是段云鹤在百草堂时对曲龄幽的称呼。
现在她也这么唤曲龄幽。
她的眼睛里也有希冀。
和月三除了希冀外面无表情、隐约疏离不同,明墨额头上出了汗,眼角有泪花,漆黑的眼睛明亮有光,正亮晶晶、满怀希望地看过来。
她希望什么不用说也知道。
曲龄幽顶着左右两道目光,头有些疼。
理智上她知道月三是对的。
虽然不知道明墨是怎么回事,但那药是她手下贴身带着、一到曲府就接管了厨房亲自煎出来的,肯定是适合明墨的。
但情感上,她很能理解明墨。
对于平日身体健康偶尔生病的人来说,喝药有什么难的?不过是一仰头一吞咽的事。
但对那些经常生病、和药为伍的人来说,有时候喝药就是很难,难于上青天。
难得的不讲理任性,背后有数不清的苦涩不甘。
“龄幽。”明墨又喊了她一声,声音放缓、语调温柔,就跟撒娇一样。
曲龄幽的心因而软了软。
“把药拿出去吧。”她轻叹一声,迎着月三不赞同的眼神,平缓而坚定:“你们也出去。”
月十四迟疑了一下,拉着月三出去,顺便很贴心地把门关上了。
曲龄幽走到床前,坐下,伸手去扯明墨的被子。
对上明墨警惕的眼神,她失笑:“你要一直闷在被子里吗?”
她顿了顿,接着道:“你闷死不要紧,但这是我的床、我的被子,我还要睡、还要盖的。”
她继续扯被子。
这回被子松松软软被她扯开了。
她看着外衣都来不及脱躺在床上不住颤抖的明墨,再接再厉去脱明墨的衣服。
明墨也不反抗,很乖巧地任由她解开厚厚几层衣服,到最后就剩一层里衣。
衣襟要松不松的,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,汗汇成水滴正淌下。
曲龄幽看了一眼,像是被什么烫了一下,逃也似的移开了目光。
她将明墨染了血的几件外衣拿出来,再把被子给她盖回去。
然后要做什么呢?曲龄幽有些无措。
明墨不想喝药,但痛却没有停止。
往日别说被她脱到只剩里衣,只怕她多看几眼明墨就能脸红。
现在明墨却没有反应,一看就是痛到不行了。
她边想边拿帕子擦掉明墨唇角的血迹。
虽然速度很慢,但她唇角一直有血溢出。
“明墨,你是病了么?”她问,既希望明墨跟她说话能转移注意力不那么痛,也是真的想不明白。
在百草堂明墨吐血时,她让坐堂的陈大夫给明墨看过。
但是什么都看不出来。
单从脉象看,明墨的身体没有问题。
是陈大夫医术不精,还是明墨有什么隐疾?
“不是病。”明墨闻着苦涩药味散去后属于曲龄幽的味道,仰着头看曲龄幽,声音轻轻地、慢慢地,像是沉进了某段回忆:“是蛊。”
蛊?
曲龄幽心头微震。
“怎么会是蛊?那东西不是百年前——”她说着看到明墨脸上很明显惊讶的表情,有些不悦:“你什么表情?以为我只是商人,就不配知道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