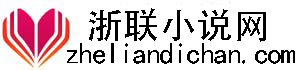第44章 仓法——北宋时期的“重禄治赃”(1/3)
元佑七年(1092),三月十六日。苏东坡在颍州时就开始着手与赵德麟同治的西湖疏浚工程,终于完成了,赵德麟寄诗来,东坡高兴之余和诗三首。
“朅来颍尾弄秋色,一水萦带昭灵宫。坐思吴越不可到,借君月斧修朣胧。二十四桥亦何有,换此十顷玻璃风。”正是由于苏东坡主持了对西湖的美化,并广植绿树菱荷,增益亭台阁堂等,才使古代颍州西湖以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园林建筑闻名于世。
“大千起灭一尘里,未觉杭颍谁雌雄。”东坡先生甚至还在其诗中将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,此举大大提高了颍州西湖的声誉。宋代以后,颍州西湖的名气大增。正是由于欧阳修、苏东坡等文人知州们的精心治理和倾力打造,颍州西湖才名扬天下、享誉千年。
苏东坡到扬州任后一直忙于事务,根本抽不出时间会客。
这天,两浙转运副使毛渐(字正仲)给东坡送来了茶叶,东坡就趁机约了几位朋友聚集于扬州西门外的石塔寺。
石塔寺本晋代遗刹,名蒙因显庆禅院。南朝宋元嘉十七年(440年),改为惠昭寺。唐先天元年(712年),又改名安国寺,乾元中(758-778年)始更名“木兰院”,开成三年(838年),得佛舍利于木兰院,建石塔藏之,故易名石塔寺。
“尔来又衰病,过午食辄噎。缪为淮海帅,每愧厨传缺。”时年已五十七岁的东坡先生,胃口也不行了,还一身的疾患。他在诗中自嘲说,自己虽然身为一州之守,但每每感到厨房里的食物短缺。
原因是,扬州位于东南方位,本来是一座都会,“八路舟车,无不由此。使客杂还,馈送相望,将迎之费,相继不绝。”,但是该州每年的公使额钱,只与真州、泗州等列郡一般,比之楚州,少七百贯。扬州与杭州的体量差不多,杭州的公使钱有七千贯,而扬州只有五千贯,显然支使不足。
石塔寺诸人聚会结束后,东坡先生到任以来一直忧虑的事情又浮现在心头。那就是,如今太皇太后与陛下已经执政八年有余,不管是仁政、德行还是节俭等方面都已经做到了极致。本来百姓应该安居乐业的,但由于陈年的积欠使得百姓们压得喘不过气来,都已经是濒临破产的边缘。
苏东坡又向朝廷上书,就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并上奏,洋洋洒洒地写了数千言,贴黄又贴黄。真是知无不言,意犹未尽,一片忠心跃然纸上。
上了奏章,苏东坡的心里一点也不轻松,他不知道朝廷会不会如愿将老百姓的陈年积欠免除殆尽,让百姓们轻装上阵,去寻求自己的美满生活。
他忧心忡忡地来到了晁补之的“随斋”以消暑,赋《减字木兰花》抒怀,算是暂时忘却一下心中的忧愁吧。东坡的心情刚刚有点平复,就听到了被自己称为“慷慨奇士,博学能诗”的老朋友刘景文卒于隰州官所。
刘景文父亲刘平作为环庆将官,曾在对抗西夏元昊的战争中,壮烈殉国。朝廷赐予了刘平七个儿子豪宅与官职,但七个儿子中的六个(庆孙、贻孙、宜孙、昌孙、保孙、季孙)都早逝了,仅剩的刘季孙(字景文)也是在六十岁年纪上才官至文思副使。
如今,这位幸存者也离世了,敢于孤军救援延州,终因寡不敌众而绝食而死的刘平将军的七个儿子都已寿终正寝了。
面对扬州周边几个州的百姓因为饥馑与瘟疫流行而流离失所、伤亡过半,并且还背负着沉重的积欠钱物的负担,老百姓卖房卖地、卖儿卖女也无法摆脱的现状,东坡先生只好给远在颍州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