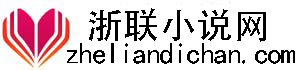第121章 盐政(1/4)
紫禁城的清晨,乳白的薄雾还在飞檐斗拱间萦绕。熹微的晨光刺破云层,将琉璃瓦上凝结的夜露映得晶莹剔透,折射出碎钻般的光芒,却始终无法驱散林璃心头的阴霾。她端坐在紫檀雕花的书房内,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案头鎏金螭纹镇纸,面前堆成小山的密折用明黄缎带捆扎,每一份都系着事关社稷安危的朱漆火漆印。"公主殿下," 贴身侍女素心捧着鎏银茶壶,轻手轻脚踏入门槛,绣鞋踏在青砖上几乎没发出声响,"卯时三刻煮的碧螺春,这会儿怕是凉透了,奴婢再去换壶新茶?"
林璃恍若未闻,苍白的指尖捏着最新送来的密折,宣纸在烛火下透出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。这是江南织造府暗桩通过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密函,火漆印上特有的 "梅" 字暗纹,昭示着信息来源的绝对可靠。她忽然重重将密折拍在案上,震得笔洗里的墨汁泛起涟漪:"好个八爷党,真是阴魂不散!"
案头铜漏 "滴答" 作响,更衬得室内死寂。林璃起身踱至窗前,望着远处角楼飞檐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记忆突然被拉回三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夺嫡之争,八爷胤禩一党树大根深,朝堂内外遍布眼线,若非先帝临终前早有安排,这江山社稷险些易主。如今蛰伏许久的残余势力,竟把主意打到了盐政上。
私盐一事,向来是悬在朝廷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自顺治年间推行 "引岸制",食盐专卖权牢牢攥在朝廷手中,每斤官盐的利润都化作充盈国库的白银。但在利益驱使下,江浙沿海的盐枭与地方豪强勾结,私开盐灶、偷运私盐。这些私盐价格只有官盐的三分之一,虽掺杂泥沙、苦涩难咽,却因价廉引得百姓争相购买。如今八爷党余孽不仅垄断两淮私盐渠道,更勾结漕帮,用运粮的官船夹带私盐,致使扬州盐运衙门近三月盐税锐减七成。
"素心," 林璃突然转身,凤目闪过寒光,"去将内务府赵公公请来,再备一份八百里加急,传信给两江总督衙门。" 她摩挲着密折上某处批注,那里用朱砂画着个醒目的圈 ——"漕运总督府有内应",这短短七字,仿佛撕开了一张庞大的贪腐黑网。
“来人,” 林璃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案头青玉镇纸,声音穿透雕花木窗惊飞檐下雀鸟,“传我的命令,让李卫即刻进宫见我。” 檐角铜铃叮咚作响,将她眼底转瞬即逝的冷芒碎成点点寒星。
李卫,时任江苏巡抚,此刻正策马疾驰在紫禁城蜿蜒的甬道上。这位出身微末却官运亨通的能吏,腰间绣春刀随着颠簸发出清越轻鸣。半月前他刚在扬州截获三艘满载私盐的漕船,船帮上那抹暗金鸢尾纹,正是八爷党残余势力的隐秘标记。
殿内沉香袅袅,林璃望着铜镜里自己眉间朱砂痣,想起三日前那封被血浸透的密信。信笺边缘焦黑,显然是从火场抢出,而信中 “盐引” 二字被反复描摹,墨迹早已晕染成深褐色的痂。
“吱呀 ——” 雕花木门被推开,李卫单膝跪地时,官服下摆还沾着城郊官道的黄土。他额前碎发紧贴皮肤,腰间玉带扣在晨光里折射出锐利锋芒:“卑职李卫,见过公主殿下。”
“李大人,不必多礼。” 林璃将密折推过檀木桌案,指尖在 “漕运总督府” 字样上重重一按。密折展开的瞬间,苏州河上那艘焚毁的画舫仿佛在两人眼前重现,烧焦的梁柱间漂浮着半块刻有 “盐引” 字样的竹牌。
李卫瞳孔骤缩,指节捏得密折簌簌作响。扬州漕运码头查获的假盐引,金陵钱庄突然激增的银锭,此刻如锁链般在他脑中串联。他猛地叩首,官帽红宝石撞在青砖上发出闷响:“卑职失职,请公主殿下责罚!”
林璃起身走到窗边,望着御花园中凋零的海棠轻叹:“八爷党蛰伏十年,在两淮盐场织就的罗网,岂是